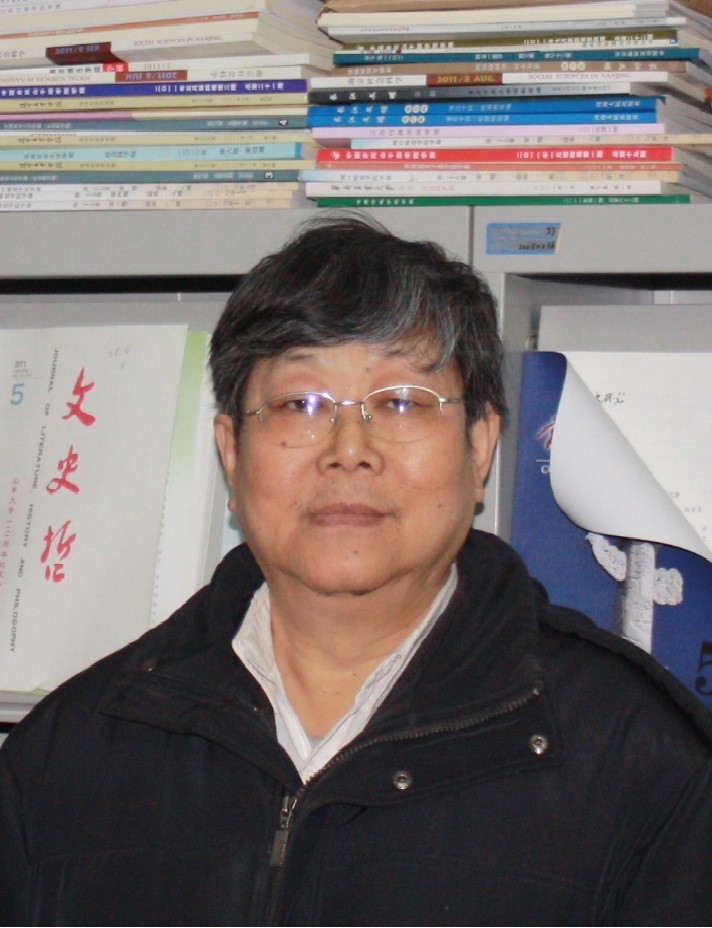
自序
我已年过花甲,人微言轻。
今天,目睹当代考古在五彩缤纷的发掘成果的掩盖下连天飞舞的学术泡沫,以及愈演愈烈的“假大空”现象,禁不住忧心忡忡,可又深感回天乏力。为此,只能独自设一个网站,籍此公共平台表达一下自己心中的郁闷与主流不尽相同而又无人问津的学术观点。
这虽然是一种无奈,但也寄托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与憧憬。
个人简介
裴安平, 1953年10月4日生于湖南安仁县,祖籍山西平遥。北京大学77级考古专业本科生,81级硕士研究生,导师苏秉琦、俞伟超。
1985—2002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先后主持澧县彭头山、澧县八十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发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对中国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稻作农业、文明起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序列的研究成果突出。1994年八十垱遗址发掘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三等奖,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获湖南省文化系统一等奖。2002年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工作,任教授、博导、考古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1990、2001、2010、2017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普通项目二项,后期资助项目一项。
已正式出版的代表作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第一作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农业•文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史前稻作研究文集》(第一作者,科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书局2014年)、《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与前瞻》(2022年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此外,2016年《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外译(英语)项目。202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德国Springer正式出版。2020年《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又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外译(英语)项目,将于2024年由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德国Springer正式出版。
近年被打压和排斥大事记
1、近20年来,《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中国文物报》没有发过我一篇文章;全国各文物考古刊物也不敢发我的文章。不是我没有投搞,而是都退回来了。
2、由于我是苏秉琦、俞伟超先生为数很少的学生之一,所以近20年来只到北京大学参加过他们的纪念会。此外,没有人邀请我参加过任何一次全国性的考古会议,即使是史前研究会也不让我参加。
3、虽然我曾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对湖南省的文物考古事业贡献颇大,但近20年来湖南省从未邀请我参加过任何考古会议。
4、2013年,由于《南方文物》发表了我的《山西临汾盆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文,有人对此表示了不满。于是,《南方文物》办刊“要讲政治”,再也不敢发我的文章了。
5、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靠前宣读了《文明探源,源在何方》一文。可是,会后有人打电话给湖北,要他们不要发表我的文章;以后也不要请我开会,因为我到处放炮。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湖北考古人,他们居然顶住压力,在会议论文集的最后发表了我的文章。
6、2013年,由于我事先打了招呼,因而有幸在榆林参加了当年的石峁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事先提交了论文。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会议领导会把我这个全国考古界都知道的老考古人安排在科技组参会和发言。尽管我当时就向会议领导提出了要求换到考古组的请求,但没有反应,而且会议最后的总结也没有提及我的意见和看法。
7、由于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我的论文集,所以我的《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和前瞻》只能拿到台湾花木兰出版(2022年)。
这就是近20年来,因为我认为中国文明探源走错了路,要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之路,所以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连参会发言和发表文章的机会与权力都不给。今天,北京大学和山东考古所发表了大汶口文化傳家遗址的DNA研究报告,证实血缘社会确实存在聚落群聚现象。我很高兴,也认为是时候要为我平反了。
实际上,我的错顶多也就是没有为现代讨好上级的文明探源工程增光添色而已。千万不要把不同学术观点当作阶级斗争,无情排斥,残酷打压。
悲矣!
邮箱地址
peianping1953@126.com